黎嘉翰 大埔區院牧事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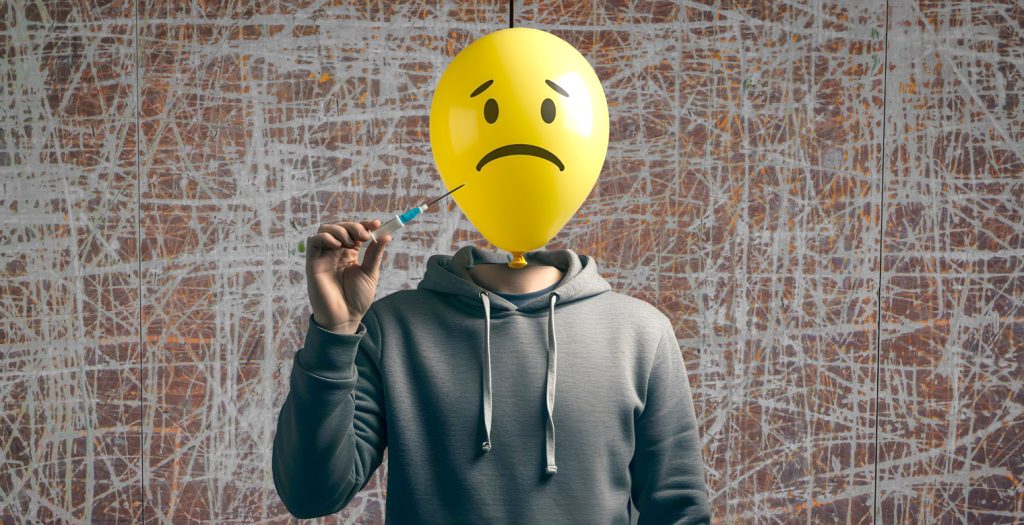
個案:
史提芬(化名)是一位單身中年人,癌症擴散讓他的身體癱瘓,器官衰竭。發病五年,患病導致他失去聽力和說話的能力,只剩下可以活動的雙手和清醒的頭腦。這樣的日子,對他而言是無盡的折磨。然而,每次探訪總見他雙手被約束,據悉是為了防範一切的「危機」發生。探訪前,我總得向醫護人員溝通一下,盼能把約束帶稍微鬆綁,讓他至少能用一隻手握著筆,以文字與我交流。然而,雙手仍被約束帶限制了活動範圍,他要費盡力氣才能勉強寫下幾個字。這樣的溝通,緩慢而艱難,需要我額外的觀察力與耐心才行。
好不容易等到他寫下幾個字,卻總是直擊心坎的三個字——「我想死!」這短短的字句,承載了他對生存意義的深深質疑,也透露出被照顧時尊嚴被剝奪的無奈。皆因無論是排泄、洗澡還是轉身這些尋常小事,他都需要別人幫忙。父母早已離世,生命中僅有的依靠,是一位不辭勞苦的姊姊像母親一樣照顧著他。她每每溫言鼓勵,希望弟弟能振作起來。可是史提芬卻一次又一次用文字傾訴想死的念頭,實情是身體衰弱到連自殺的力氣都沒有,唯一的雙手也被約束起來,筆下滿是憤怒與無助。每當我看著他,心中總被他的苦難觸動,默默與他一起仰望那掌管生命的主。
反省:尊嚴何在?
史提芬的處境讓我不住地想,尊嚴究竟是甚麼?在如此痛不欲生的光景中,他對生命的意義和自身的價值充滿疑問:當身體一點點崩塌,尊嚴是否也隨之消逝?人是否能以「有尊嚴」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?作為院牧,我無法忽視他的痛苦,內心卻在信仰與現實的苦難間撕扯:一方面巴不得上天可以抹去他的勞苦,另一方面我深知生死的權柄在神手中,並不在我們。
生命的主權與神的形象
基督信仰詮釋我們的生命皆是神的「禮物」,是祂親手賜下的恩典。人類是「第六日的受造物」,由神賦予靈性生命(創2:7),因此生命的本源屬於神,而非完全屬於自己。創世記1:26記載,神說:「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,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……」這表明人按神的形象被造,擁有內在的尊嚴(intrinsic dignity),不因健康狀況、社會地位或能力而改變。詩篇8:5亦說:「你使他比神微小一點,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。」即使罪惡扭曲了我們的人性,神仍通過基督的救贖使萬有與祂和好(歌羅西書1:19-20)。所以,史提芬的尊嚴,並未因癌症而被奪去。
然而,死亡(包括面對邁向死亡)是人類「有限性」的體現,也是罪的後果。但基督的復活戰勝了死亡,為我們帶來永生的盼望。無論身處怎樣的光景,生命依然映照著神的形象。我們來到這世界,也將離開這世界,都是在祂溫暖的掌心之中。作為院牧,我無法越過神對史提芬生命的安排,也難以支持他自尋短見,或許這只是用一種「強行關機」的方式逃避人生的無奈,卻無法真正撫平心底的遺憾。
人性的脆弱與相互依靠
細想人性,我們其實是多麼脆弱。從呱呱墜地那一刻起,細菌、病毒、意外、病痛就環繞四周。即使躲過重重劫難,也逃不過生老病死。然而,神卻以道成肉身的形象降到這世間,甘願受盡鞭打與流血。那十字架上殘破的身軀雖不完美,卻依然神聖。這讓我們明白,病痛或殘缺從不意味著神的愛已遠離。
那麼,面對像史提芬這樣幾乎失去所有機能的人,我們能做甚麼?
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(哥林多前書12 : 12 – 27),啟示我們弱者需要被關懷,這是人被造的必然經驗,也是神的形象中的重要部分。就像初生的孩子需要全家人的照顧,卻無人覺得羞恥,病者的需要也不應因病情是否好轉而被忽視。人與人的相處,本就是相互依存(interdependence)的關係,沒有人能獨立生存而永遠長壽健康。這種相互依存,正是個人與主相遇的時刻。多少信仰的見證,都是群體攜手、一起走過風雨的美事。
有尊嚴的死亡與文化的扭曲
人總是害怕痛苦,渴望離世時能安詳無痛,彷彿只有這樣才是蒙受慈愛。然而,現實中許多人生終結時並不如此。當傷病折磨到難以忍受的地步,我深知自殺並非真正的「無痛」解脫,更不能為生命留下尊嚴。即使在痛苦中走向生命的終點,尊嚴也不會因此被剝奪。我明白選擇活下去,有時比離開需要更大的付出,但若以死亡來逃避不願面對的生命樣貌,這並非對生命的珍重。死亡中的尊嚴,不在於能否躲開苦楚或自己決定終結,而在於我們如何在生命最後的時光裡,依然懷著一顆敬重與珍惜的心,去擁抱每一個艱難的瞬間。是否安詳地離去,與尊嚴並無必然的聯繫。病人在臨終時的掙扎與無奈,也從不意味著神的慈愛已遠離他們。
當今的文化卻常把尊嚴與無痛、自主綁在一起,甚至認為只有無痛苦的離去才有尊嚴。可是這樣的觀念,我擔心有時帶來更大的傷害。尤其在亞洲的文化中,尊嚴常被繫於面子、地位或成就,以致像殘疾人士或長者的群體被忽視,甚至被輕看。當社會將病痛中的依賴視為「無尊嚴」或「羞恥」,便把問題推到受苦者身上,認為「人口老化」、「長命」令整個社會都承受沉重的壓力。這不僅無助於照顧與康復,反而剝奪病人的權益,久而久之,自殺竟成為某些人的選項。
結語:綻放尊嚴的生命
誰有資格說,哪一個生命不值得活下去?作為信仰群體,我們要用愛反轉這樣的世俗眼光,堅定地相信:照顧病者是人性中最溫暖的責任,也是最榮耀的事。美善的照顧是體現生命應有的尊嚴,因此眾教會應當給予病者最真摯的關懷,讓他們在最虛弱的日子裡,依然能綻放出生命的尊嚴。這份尊嚴,離不開同舟共濟的家人、用心聆聽的牧者、細膩體貼的醫護、默默陪伴的義工,以及仁民愛物的決策領袖。
史提芬撕心裂肺地呼喊「我想死」,像一記警鐘,敲醒我們每一個人:生命雖有盡頭,尊嚴卻是神所賜的珍寶。我們或許無法改變他的處境,但可以陪他走過這段路,讓他在苦痛中感受到神的溫暖與人的關愛。這正是院牧工作的圖畫——在苦難中見證神作工的身影,在絕望中點亮盼望的微光。


